公主的扇子:神秘魅力与时尚风潮

关注 ▲书艺公社▲ 与万千书坛精英,
探寻醉中国的书画印生活新方式!
对中国人来说,“百子图”大概是最知名的吉祥主题。多子多福,一直是上至皇帝、下至老百姓的共同梦想。位于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城的克利夫兰美术馆藏有一件精巧的《百子图》团扇(图1),这件南宋时代的杰作是现存最早的一幅百子图。不过,或许是由于百子图的主题过于司空见惯,寓意过于明显,对这件团扇的研究并不太多。实际上,这件常常被忽视的精巧扇面是我们认识百子图以及理解南宋绘画的一个绝佳案例。
方寸之内的儿戏
和一般的团扇一样,保存在克利夫兰的《百子图》也是画在质量上乘的绢上,经历近千年,保存依然完好。可惜的是,艺术史家尚没有给予这幅画足够的重视。相形之下,戏剧史家倒是对此画充满兴趣。早在1991年,戏剧史家周华斌就曾发表《南宋〈百子杂剧图〉考释》一文,对这幅团扇的时代、内容进行了考察。戏剧史家之所以有兴趣,在于画中儿童所从事的,全都是各种各样的杂剧表演。由于古代戏剧表演的实况我们早已不能见到,因此,描绘戏剧表演的图画就成为戏剧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证据。不过,这种方式也会带来一个问题:“百子图”属于吉祥绘画,自然不会是宋代戏剧场景完全真实的再现。那么,画中究竟有多少是现实,又有多少是理想?
《百子图》团扇纵28.8厘米,横31.3厘米,比一般的宋代团扇略大一些。画中儿童看似嘈杂,实则排列井然有序。耐心数一数,恰好一百整,证明《百子图》实至名归。百子分成左右两边,每边正好五十个。这种区分是为了避开扇面中间的一条扇骨。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放进博物馆中的古画,而在当时,与其说是画,不如说是一面扇子,用来遮面,或者扇凉。团扇中,每一边都分成下、中、上三组。扇面左右两边相呼应,一共是六组表演队伍。每一组都可分成外围的乐队、中心的演员以及穿插其中的龙套。
如此安排体现出画家的匠心。实际上,如果仔细观察团扇左右两边的表演内容,可以看到它有着不同的侧重。
先看团扇的左边。
下部的表演以三位身着异族服装的歌舞者为中心,尤其是面对面舞蹈的一对,背面的是男性,正面的是女性。
中部的表演核心是呈三足鼎立姿态的三位化装人物(图2),一位拿着硕大的毛笔,身穿宋代低级文官的青袍,头戴宋代官帽展脚幞头;一位黑衣黑巾,脚穿木屐,手拿铜钹;还有一位穿着红袍,头戴戒箍。周华斌先生认为表现的可能是“闹学堂”。其实,这一幕应该是“乔三教”。“乔”意为“乔装打扮”,即装扮成儒、释、道三教形象进行表演。戴官帽、扛毛笔的无疑是“儒”,所谓“学而优则仕”,一切全靠一支笔,通过笔来考试,通过笔来治国。在三人中,他占据中心,这正是儒家地位的显示。右边黑衣人头戴的是南宋隐士常戴的头巾,在南宋绘画中多有表现。比较特别的是他脚踏木屐,木屐可能是强调其隐士的身份。黑头巾、黑袍以及木屐,都是在指向隐者,而道家往往与隐相关,所以这个形象应为“道”。红袈裟、戴戒箍的是头陀打扮,脚蹬草鞋,是行脚僧,应为“释”。三教中,每一教都非典型形象,而这正是表演的噱头。
图2 《百子图》局部
最上部表演的是“竹马”(图3)。在这里,两个小孩套着竹马,手拿旗帜,似乎在打斗。他们戴着类似北方少数民族的帽子。前面还有两位拿着盾牌的军士,究竟是表现什么故事尚不知晓,周华斌认为可能是所谓的“双排军”等,即装扮成两个兵丁进行滑稽表演。不过我觉得其他可能也很大,譬如“蛮牌”。“蛮牌”即盾牌,所谓“蛮牌”表演就是舞盾牌或者是滑稽的格斗。
 图3 《百子图》局部
图3 《百子图》局部倘若要归类,团扇左边的这些表演内容大多与国家事务有关。外族人的舞蹈、儒释道三教的关系,或者是胡人的进贡、疆场厮杀,这些都属于国家大事。而团扇右边的表演内容截然不同,大多是一些滑稽的日常事务。下部的核心是一对打着伞盖的公婆;中部的核心是一对年轻一些的夫妇,妇人手中抱着幼婴。周华斌认为可能是文献记载的所谓“乔亲事”或“乔宅眷”之类。上部的中心是一个装扮成仙鹤的人物,旁边还有几个滑稽形象,围着仙鹤。周华斌认为是渔民形象,手拿的是渔网或船桨,表现的是“渔家乐”。不过更有可能的是,弓腰背着仙鹤道具的儿童可能就是所谓的“乔像生”,即模仿各种人、动物进行表演。而所谓的“桨形物”,则是巨大的、需要扛着或拖着的大瓜,一头的瓜蒂也清晰可辨。
如果说团扇左边是“国”与政治事务,那么团扇右边就是“家”与日常琐事,合起来构成一个完美的“内”“外”均衡与“国家”概念。画家的匠心渐渐显露出来,然而却不是到此为止。画家为何要如此殚精竭虑,于方寸之地经营出如此精细的造型,究竟要满足谁的欣赏眼光?
百子图与宫廷婚礼
虽然描绘婴儿早在唐代就很流行,但“百子图”这个主题恐怕要到南宋才产生。辛弃疾有一首《鹧鸪天》,吟咏的是友人庭院里一株开了百朵的牡丹花。词人先描述了牡丹娇艳欲滴的状貌,最后将这株牡丹比作一幅“百子图”:“恰如翠幕高堂上,来看红衫百子图。”“翠幕高堂”以及“红衫”,常用来代表婚礼,“百子图”一词用在这里,似乎也有婚礼的寓意。所谓“红衫百子图”,似乎是指大红色的婚袍上绣的百子图。
无独有偶,辛弃疾的同时代人、南宋孝宗时的官僚姜特立用了另一个词“椒房百子图”,说明“百子图”与皇室女性关系密切。姜特立一次赠送友人刘公达一扇放在床头的小屏风和一个竹炉,并作诗一首:“不画椒房百子图,销金帐下拥流苏。聊将鸥鹭沧州趣,伴送江西古竹炉。”他调侃自己不送椒房中所用的“百子图”给刘公达,而是送一个能够让人产生隐居之心的枕屏。“椒房”代指的是皇后与皇妃等宫廷女性。姜特立提到,“百子图”是在“销金帐下拥流苏”时使用的。“销金帐”是一种极为贵重的织物,指装饰着金线的床帐。在南宋,一般的城市富裕家庭用得起销金头巾等物,但尺寸巨大的销金帐却只有皇室才用得起。在姜特立看来,“百子图”就是在皇后的寝宫中欣赏的图画。那么,后宫为何需要“百子图”呢?答案是用作婚礼。
“百子”是吉祥的名字,在唐代人的婚礼中,就有一种帐子叫作“百子帐”。南宋人程大昌在《演繁露》中专门考证了这种“百子帐”的来源,认为这种帐子实际上源于游牧民族的穹隆形帐篷,由于支撑帐篷需要用到将近一百个相互扣连的圆环而被称为“百子帐”。因为名称十分吉祥,被唐人用于婚礼。在南宋人的《枫窗小牍》中,则有对程大昌考证的再考证。在引用程大昌的考证之后,作者说道:
若今禁中大婚百子帐,则以锦绣织成百子儿嬉戏状,非若程(大昌)说矣。
这里提到一个重要的现象,即南宋皇宫中婚礼所用的“百子帐”已经不再是程大昌所说的模仿自游牧民族的穹隆顶帐篷,所谓的“百子”,也不再是支撑帐篷的构件,而是绣在床帐上的百子嬉戏的图画。
既然一百名儿童嬉戏的图像是南宋宫廷新出现的婚礼吉祥主题,那么我们可以推想,克利夫兰美术馆的《百子图》团扇,也应该是皇室婚礼所用的一件吉祥图画。画中于皇家庭院中表演着各种杂剧、歌舞的儿童,既象征着婚礼庆典时的盛大表演,也象征着皇宫女性为皇室生育健康活泼的子嗣。
画中的孩童数量恰好一百个,在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可能这么多的孩童同时进行表演?有可能,不过是在皇宫中。
宋代宫廷宴会的表演中,有一种“小儿队”,分为十个小队,共七十二人,以歌舞为主,也穿插有杂戏表演。如此热闹的表演场景,即便在皇宫中也只出现在重大的庆典之中,譬如元宵节。《百子图》团扇虽然并非是对小儿队表演的真实写照,但画家的灵感似乎正是来源于此,也只有为宫廷服务的画家才有这种能力和机会。
一个奇怪的地方是,除了克利夫兰的这幅画,在存世的其他百子图中,我们都看不到儿童表演杂剧的场景。儿童通常从事的是各种儿童游戏,比如蹴鞠、打陀螺、点炮仗、放风筝等等。这些游戏大多是适合儿童的游戏,也有一些模仿大人的游戏,比如赏画、下棋。总体来说,是孩子们自娱自乐的游戏,而不是演出来供人欣赏的杂剧。像克利夫兰《百子图》这般严整的杂剧表演阵容,如此专业的道具、化装和表演,仅此一例。究竟是谁的婚礼值得如此庆祝?
“鞑靼舞”和宋理宗时代
解开这个谜团的关键是画中两个特别的场景。
周华斌最先注意到画中有身着异族服装跳舞以及进行竹马表演的景象,不过他认为服饰是女真人的。跳舞的一对儿童身穿紧身的长袍,头戴圆顶帽。进行竹马表演的三个儿童则头戴尖顶帽。不论是圆顶还是尖顶,必是北方民族的服饰无疑。在南宋时代,与其共存的外族政权主要是女真人的金、党项人的西夏和蒙古人的元。通过考古出土的金、元墓葬中的陶俑和壁画可以看到,不论是尖顶还是圆顶笠帽,主要是女真人和蒙古人的服饰,尤其是《百子图》中跳舞的儿童头戴的圆顶帽,扮作女性的那位帽边有毛边,扮作男性的那位帽子分成几块,接近所谓的“瓦楞帽”,都是蒙古人常见的装束(图4)。

有趣的是,在南宋后期的临安城,确实流行蒙古人的舞蹈。《西湖老人繁盛录》记载,当时有“鞑靼舞”“老番人”两种舞蹈。“鞑靼”是南宋人对蒙古人的称呼。《百子图》中的蒙古乐舞,应该就是这种“鞑靼舞”。
《西湖老人繁盛录》没有作者的姓名,我们甚至不知道具体的年代。不过,书中所记载的几位表演傀儡戏的著名艺人,其名字同样出现在吴自牧的《梦粱录》中,而吴自牧明确提到他们是宋理宗时的艺人。因此,《西湖老人繁盛录》应该是南宋末年宋理宗时期(1224—1264)的一本著作。那么,“鞑靼舞”应该也是理宗时的新鲜事物了。
宋理宗在位四十一年,堪称南宋最好的一段统治时期。正是在理宗朝,威胁大宋一百余年的金被南宋与蒙古联军剿灭,北宋的大仇得报。之后,蒙古虽然试图灭亡南宋,但时机未到,反而屡次被南宋击败。当时,曾经威胁过宋朝的辽、金、西夏均已灭亡,只剩一个蒙古。因此,宋理宗在位的这段时光,对于南宋来说,似乎是一段少有的和平年代。
“鞑靼舞”在临安的流行,应该是与宋理宗时期和蒙古的战争有关。一则当时宋、蒙双方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经济与文化交流相对频繁。二则南宋宫廷也可能是用蒙古歌舞来标榜对蒙古作战的一系列胜利。这在中国历史中屡见不鲜,譬如汉武帝征服西域,西域葡萄便进入了中原。儿童们模仿蒙古人的舞蹈以及蒙古军的装扮进行表演,将时事与娱乐融合在一起。这幅团扇的绘制年代,最有可能是在蒙古与南宋联手灭金之后,亦即1234年之后。
末代公主
如果将克利夫兰《百子图》的年代定在宋理宗时期,而且是在金朝灭亡之后,那么我们便可以有机会来推知这幅绘画的上下文。
皇家婚礼实际上不外乎几种:皇帝大婚、皇子娶妇、公主下降。崇尚道学的宋理宗只有一位皇后谢道清。理宗一生无子,只有一位公主长大成人。因此,在宋理宗朝,有可能举行婚礼的只有宋理宗本人以及公主。宋理宗与谢道清的婚礼是在理宗即位后不久的绍定三年(1230),这时金还没有灭亡,蒙古还没有完全取代金成为南宋最大的威胁。因此,只剩下最后一种可能——理宗的掌上明珠、周汉国公主的婚礼。实际上,公主不仅是理宗唯一的子女,也是整个南宋唯一长大成人的公主。因此,她的婚礼极其隆重,南宋末、元代初年的著名文人周密在《武林旧事》中给予了长篇描述。公主的驸马是宋理宗的母后杨皇后的侄孙杨镇。因为娶的是公主,男方家出的聘礼极多,包括“红罗百匹、银器百两、衣着百匹,聘财银一万两”。当然,这些都是皇帝事先赏赐给杨镇的,皇帝嫁女,自然所有的事都是皇家“三包”。为了显示婚礼的规格,皇帝还下令所有的朝中高官都到皇宫中来欣赏公主盛大的嫁妆。公主婚礼前后七个月,从景定二年(1261)四月的订婚持续到十一月的迎娶。十一月十九日是最隆重的迎亲仪式。这天,除了不能轻易离开皇宫的皇帝之外,所有的皇室成员,包括皇后、皇太子、皇弟荣王夫妇全部来送公主至驸马家,阵容超级豪华。婚礼三天之后,公主夫妇回女方家,皇帝赐给各种礼物,同时在皇宫内举办大型宴会。
皇帝嫁女,自然是朝中各位权贵迎逢上意的绝好机会。他们的贺礼称作“添房”。珠领、宝花、金银器自不在话下,最有新意的是时为平江发运使的马天骥,他献上罗钿细柳箱笼百只、镀金银锁百具、锦袱百条,更绝的是,百条锦袱之中装了芝楮百万,据说“理宗为之大喜”。
在如此奢华的婚礼之中,一把小小的百子图团扇自然很容易被记述者遗漏,通常,没有人的目光能够从那些夺目的珍珠和闪耀的金银上移开。一柄不打眼的团扇,更可能是皇帝父亲日常赏赐的礼物。宫廷的团扇通常是在一些应景节日作为皇家礼物赏赐给皇族与大臣的。在存世的南宋绘画中,其实还有一件是宋理宗赏赐给公主的。这幅画曾是方形的册页,一面是宫廷画家马麟的画,一面是理宗的书法。两面如今被装裱在一起,形成一幅小立轴,这就是藏于东京根津美术馆的《夕阳秋色图》(图5)。理宗题写道:“山含秋色近,燕渡夕阳迟。赐公主。”画中钤有“甲寅”印章,为1254年,公主时年十五岁。在前一年的年底刚刚进封为“瑞国公主”,这幅画大概是对新封的瑞国公主的特别赏赐。而一件描绘百名儿童搬演歌舞杂剧的百子图团扇,在一个天气渐暖的时节,赏赐给婚后的爱女,此情此景,大概没有比这更好的皇家礼物了。
 图5 马麟《夕阳秋色图》 轴 绢本设色 51.3厘米×26.6厘米 日本根津美术馆
图5 马麟《夕阳秋色图》 轴 绢本设色 51.3厘米×26.6厘米 日本根津美术馆可惜,集万千宠爱在一身的公主,依然没有逃脱皇室的宿命,婚后第二年七月,周汉国公主不幸去世,无子,年仅二十三岁。“帝哭之甚哀”,理宗整整五天没有上朝,并且破天荒要求亲临驸马家祭奠爱女。驸马杨镇谢绝了五次,终究还是让皇帝去了。
周汉国公主堪称南宋后期的超级明星,公主的婚礼制造出了南宋最后一丝奢华景象。甚至,宋理宗还把自己游览西湖时乘的香楠木御舟赏赐给公主夫妇,下旨要求公主和驸马一起游湖。当时景象,周密在《武林旧事》中有所描述:
一时文物亦盛,仿佛承平之旧,倾城纵观,都人为之罢市。
到底,南宋消失了,御舟消失了,公主也消失了,唯有图画留存下来,记录下公主最美好的生命瞬间以及南宋的最后光华。
图文综合来源网络,分享此文旨在传递更多有价值信息之目的。和万千书坛精英,一起探寻醉中国的书画印生活新方式!原文不代表书艺公社观点、立场以及价值判断。如有关于作品内容、版权或其它问题,请与书艺公社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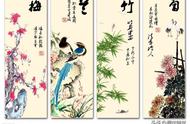















 鲁公网安备37020202000739号
鲁公网安备37020202000739号